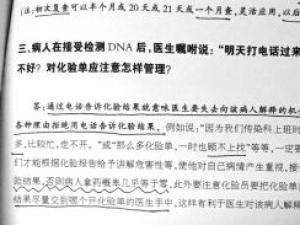《女友被调戏 浙江40多个少年深夜群殴15岁少年被6人砸死(二)》是由大铁棍娱乐网(www.datiegun.com)编辑为你整理收集在【社会万象】栏目,于2016-05-04 11:14:24整理发布,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可及时向我们反馈。
冲上来的小毛和同伴,再没给这个老乡站起来的机会。龙龙被逼到角落,6个男孩将他围拢,抄起手上的家伙,一下又一下地砸向他。
瘦小的龙龙的额头很快肿成一个大包,鲜血从鼻子和嘴巴不断涌出,不到半分钟,他就再也发不出求饶声了。
后来,经法医鉴定,那长达几十秒的施暴,对这个云南少年造成了严重的脑内创伤。
让警方感到震惊的是,引起这场血案的冲突只是当天傍晚,小毛搂了搂小贵的女朋友。其实,当时小毛就道了歉,可小贵打电话的举动让他误以为是在叫人打架。于是,他“一股火蹿上来”,也开始叫人。
再没人能冷静下来,打架前双方还曾通过一次电话,原本打算讲和的小毛,通过电话听到了“棍棒、钢管摩擦地面的声音”,他不打算留情面了。
只是,没人想到,就因为这场小小的误会,这些少年对素不相识的龙龙大打出手,几乎“棍棍都往脑门上砸”。
据警方统计,他们中最大的19岁,最小的不过13岁。
四川人小陈第二天就在溜冰场听说了这场血案,当时警方正满镇子抓人。这个21岁的男孩也有过类似的经历。
在他的印象里,他和当时二三十个“兄弟伙”,几年前做过不少疯狂的事情,他们大白天下午4点,聚集在海宁路口,和对方“干架”。自己拿着砍刀,跑在最前面冲锋陷阵。
一场架基本持续将近5分钟,直到对方的一个人被砍伤,倒在车水马龙的海宁路口,流了一地的血。警笛声近了,他们四处逃散。
“警察就那点儿人,他们管得过来?”小陈不以为然,“打快点儿就行了,不要被抓到就行了。其他人才不得管我们呢!”
小陈的话无意间戳中了这座小镇派出所的痛处。人口10万的洪合镇,正式的警察只有二十来个,“还得算上四五个领导。”副所长俞伟祥一直在发愁人少的窘境。
他在隔壁王店镇派出所任职时,也有类似的遭遇。青少年犯案多,可警察人手永远不够。
情况再明显不过了,每天都有一群年轻人在镇上无所事事地游荡,可警察再加强巡逻的班次,也总有疏漏的时候。
尤其到了夜里,抢劫和斗殴变得稀松平常。很多女孩晚上都不敢一个人出门。
夜里,没有一处是绝对安全的地方。
一个在火锅店打工的江西男孩,前些日子深夜在店里碰上了一群云南少年,干完活儿的云南少年在火锅店点了不少酒。喝完,领头的少年就开始发疯。他砸了一桌子的碗和盘子,店里的女领班看不下去了,“你快住手,我要报警了!”
“妈的,要你管。”
少年一把扯住女领班的头发,像拿着一个碗,一下又一下地砸向桌子。碎玻璃碴划破了女领班的头,血顺着头发流下,女领班发出惊恐的尖叫声。
“简直就是恐怖片。”这个18岁的少年说,自己已经后悔来到洪合了,这里“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好”,还“特别危险”,他打算,干满这几个月,回老家复读,参加高考。
重庆男孩小罗也后悔了。他也很想离开洪合。他和父母住在永兴桥附近,一家人以套口为生。案发那天晚上,他并没有睡着,隔着窗户,他清楚地听见了怒骂声、棍棒击打声,以及龙龙的哭喊声。
可他不敢站出来。
这个少年曾目睹过几个云南文山的混混抢劫,他害怕那些人,害怕那些棍子砸在自己身上。
龙龙就这样错过了最后的获救机会。据法医透露,龙龙被打后,颅内出血严重,几乎当场失去了生还的可能。
“你要抓就抓啦,我很忙的,不想管他,你不要找我了”
血案发生第二天,警方就将几名主要嫌疑人抓获。40多个打架的孩子里,有人已经逃到了嘉兴市区,还有人准备躲回老家,而小毛,哪儿也没去,就待在隔壁镇的姐姐家里。
奇怪的是,警方第一次做笔录时,除了小毛果断承认,其他嫌疑人都清一色地回答,“不知道棍子是谁拿的”“我没有打龙龙”“哪些人打的我也没看清”……
俞伟祥对这样的答案已经见怪不怪了,“推卸责任、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大有人在。”
事实上,这场血案还夹杂了些许“设计”的味道。尽管是临时起意,但小毛和同伴还是早早赶到永兴桥头,并安排了十几个个头高、力气大的同伴躲在暗处,等到对方杀过来时,“再出来,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从警十余年,俞伟祥和很多少年犯打过交道,这些少年进派出所的次数不比回家的次数少,“面对警察一套一套的。”
这个老干警见过一个外地少年,从8岁一直偷到了18岁。一路从洪合偷到嘉兴、杭州,杭州警方抓捕他时,惊讶地发现,这个少年“打开”一辆车的车窗只需要7秒钟。这个少年个头长高了,染了一头黄发,可俞伟祥只要看一眼监控,凭背影就能认出。
“警方很多时候也没办法,像这种小孩,没到刑事责任年龄,抓了只能教育一顿放人,放出去没隔多久又犯事。”他已经有些厌倦了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
俞伟祥不再指望孩子的父母了。他曾给许多犯事少年的爸妈打电话,可对方一听是派出所,立马一副不耐烦的态度,“你要抓就抓啦,我很忙的,不想管他,你不要找我了!”
这次逮捕的多名嫌疑人都是未成年人,按照法律,在审讯时应有法定代理人到场,可他们联系后,没有一家的父母愿意来派出所。
“他们心里清楚得很,犯罪成本低,反正我们也不能把他们怎么样,大不了关几天就是了。”办案警官钱晓伟说起这个就来气,“当父母的,只管生,不管教。”
这个年轻的警官心里一直有个结。头几年,他刚工作时,遇上了一个首次偷盗的孩子,他跟孩子语重心长地讲道理,告诉他,偷盗的行为是犯法的,如果年龄再大点,是会判刑的。
那次,孩子哭得稀里哗啦,跟他承诺,“再也不会去偷东西了。”可没过多久,这孩子就因为偷盗再次被抓。这回,钱晓伟再讲道理,对方“左耳进,右耳出”。
再一次被抓进派出所时,那个孩子把头埋在胳膊里,已经拒绝和他沟通了。
“我们说的话能当饭吃么?他一晚上偷车就能挣几千块钱,你说说,他会听警察的还是那些小混混的?”这个当了5年警察的年轻人叹气。
没有什么能阻止少年案件的攀升了。30%的案件里有碎尸案、轮奸案…… 不久前震惊当地的一起轮奸案,几个外地男孩对同乡的女生下了毒手,在这几个施暴男孩眼中“不过是一件小事”。
“这些网上才有的东西,现在都发生在了洪合,还全是孩子做的,你能想象吗?”警察反问道。
“这些孩子太可怕了,在哪儿都是定时炸弹,不光是洪合,你以为北上广就不会发生吗?”有当地人看到新闻报道后,为这些孩子的残忍感到后怕。
龙龙妈妈后来才知道,血案发生半小时后,小贵和同伴才慢悠悠地赶回桥头,从一摊血迹里把龙龙拖上车,带到了镇上的宾馆。根据往常打群架的善后经验,他们买了点儿药,以为“给他擦一擦,想着等到天亮就好了”。
但龙龙毫无反应。
杀人之后,小毛甚至跟小贵打了个照面,带着胜利者的姿态听对方讲,“我们都有些不对,双方道个歉算了。”
小毛点头以示同意,随后两人言和,各回各家。
“晚上的事情解决了,他们以后不敢来了。”小毛还用几分得意的语气,向队友立刻报告了战况。
那是他以为的这场群架的结局。
“你们做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呢?”
“爸,我出事了。”
“你怎么了?”艾正品接到儿子小毛的电话时,正在老家修房子,他匆忙丢下手里的活,听着电话那头的儿子说,自己跟人打了架,好像打死了人。
“你为什么要打架啊?”他忍不住问。
“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儿子不耐烦地回答,随后拒绝了父亲自首的提议,“我不能去派出所,我这么小,他们肯定要打我。”
那是艾正品最后一次和儿子联系。此后,尽管他买了最早的航班,跨越了几千公里,也没能见上儿子。
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儿子到底为什么打架。
这个年迈的父亲有3个女儿1个儿子,小毛是最小的孩子。他总是顺着儿子,读不读书、打不打工、打什么工都听儿子的。他一直念叨着,“儿子很懂事的,以前从没惹过事。”
在他的印象里,家里套口忙起来常常是从清晨干到半夜,儿子每次都跟着一起干,也不抱怨。只是,一休息,小毛的眼睛就“掉进手机里出不来了”,儿子不怎么跟家里人说话,却喜欢对着手机傻傻发笑。
这个父亲太忙了,老家的新房、洪合的套口生意、儿子未来的婚事,桩桩件件他都得考虑。他忙到没时间在意儿子有什么爱好。
龙龙的父母也很忙。前些年,云南老家的干部发动他们一起来嘉兴挣钱。这一年,羊毛衫生意淡了,龙龙的妈妈还跑到粽叶厂洗粽叶,挣一个月2000块钱的辛苦钱。
夫妻俩已经离目标很近很近了。再等3年,儿子满18岁了,夫妻俩就会自豪地跟龙龙讲,“修房子、娶媳妇、还是买车,你选吧?爸妈能帮你做一件事。”
她几乎没有休息过。这个皮肤暗黄、挂着黑眼圈的母亲说不清自己到底住在村子哪个位置,也忘了儿子的电话号码,更记不清龙龙是哪一天突然说起,自己再也不上学了。
“打死也不去,去也是白白浪费钱。”龙龙坚决地说。父亲把龙龙拖到了学校,一转眼的工夫,孩子竟然比自己先到家。他气急了,用套口的足足50公分长的绿色传送带,狠狠地抽了儿子一顿。
但这对父母能做的,也只是如此。
“我当时让他跟我们一起来嘉兴,他还不乐意,说这边必须能上学,否则才不来。”龙龙的妈妈有些哽咽,她当时求了打工学校的校长,让儿子插了班。可夫妻俩谁也想不到,仅仅一年后,儿子就那么激烈地拒绝上学。
已经没人知道答案了,龙龙的书本上到处是乱涂乱画的痕迹,只用了一年,他的语文成绩就从七八十分掉到了27分。
儿子被打那一晚,他们以为孩子只是去了亲戚老乡家住,连个电话也没打就安心入睡了。直到夜里3点,3个“染着黄毛”的男孩敲开家门,告诉他们,“龙龙被人打了。”
在那之前,龙龙每次外出归来,都告诉父母,“跟朋友去公园玩了。”
她想都没想过,给全家人带来金钱和希望的洪合镇,竟然把孩子“染”坏了。
许多小卖铺的里屋都藏着老虎机,三五成群、 “等到18岁就可以进厂了”的辍学少年,一打老虎机就是一个上午;街边的娃娃机里,装的不是玩具娃娃,而是种类繁多的烟;地下溜冰场空气不通、音乐震得让人耳鸣,生意好的时候却足有上百个孩子。
“这里就是一个滋生细菌的地方。”洪合镇派出所副所长俞伟祥说。
血案发生那晚,小毛最早就是在溜冰场集结自己的人手。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向溜冰场老板求证当天的细节,却被他反问道:“你关了这些溜冰场,那些孩子就不犯事了吗?你们做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呢?能怎样呢?”溜冰场老板说。
“真的没有第二条路了”
龙龙没了,一家人再也打不起精神做任何事了。家里拉货的电瓶车半个月没用了,连电也没充。龙龙的妈妈决定,和老公回乡,再不要来洪合这片伤心之地。
两个女儿依然留在洪合给羊毛衫套口。龙龙妈妈最放心不下二女儿。为了便宜,二女儿和三十来个人挤在一间大出租房里,干什么也不方便。
在夫妻俩租住的九联村,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洪合镇的房租太贵了,套口时机器发出轰隆隆的响声,还会被邻居投诉。这些从西南大山深处赶来东部沿海淘金的人,只得又一次住进了农村。
龙龙所在的学校是一所私立的打工子弟校,斑驳的三层绿色小楼外,是一片废墟。
只隔了一个公交站,是镇上的中心小学,几栋5层小洋楼矗立其中,一到放学时段,车子把路口围得水泄不通,车辆鸣笛声响许久。
龙龙去世的消息,许多人不知道。几位曾经的同班同学听到龙龙的大名后,瞪大眼睛,想了许久,才说,“他总是一个人坐在第一排,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反正成绩很差。”
除此之外,再无更多的印象。
不过,像龙龙这样辍学,倒不算这所打工子弟校的新鲜事儿。一名八年级女生记得,刚开学时全班还有八十来个人, 一个学期不到,就只剩下了50个。班级也从两个变成了一个。
“没有人讨论上不上高中,都在说干什么挣钱。”一个女孩回忆,有许多和龙龙很像的男孩,“没事儿就出去打架,有人打架打到手都写不了字呢。”
不过这一切,学校校长和教导主任都予以否认。他们不承认学校有过龙龙,也不承认学生辍学,他们指责了许多孩子的父母,“孩子不学好,叫他们来学校谈话都不来。”
小陈也曾是这个学校的一员。在和过去断了来往、远离“兄弟伙”和无休无止的打架后,他已娶妻生子,跟着爸爸一起做小生意。
一次他在街上偶遇当初的“兄弟伙”,却发现一个同伴不见踪影。他随口一问,有人回他,“他死了,前段时间被人杀了。”
没有葬礼,没有讣告,那个“兄弟伙”走了。那一刻,他只感觉“庆幸”。
这也曾是龙龙的妈妈第一次来到洪合最大的感受。她和老公在广东和江西都打过工,孩子就扔在云南老家让爷爷奶奶带。那时候,工厂管得严,还要住集体宿舍,孩子根本不可能带着。
正因如此,一家人生活在一起,给羊毛衫套口,边干活儿边看孩子的机会,她几乎是一口答应了下来。女儿女婿早几年就跟着老乡来了洪合,一年能挣好几万元,还能在家陪孩子的故事总算得到了亲人的证实,更何况,“还是乡干部带着大家一起来的”,她和丈夫辞掉江西工厂的活儿,带着孩子来浙江。
当时,龙龙的奶奶去世了,爷爷老得腿也迈不动了,孩子压根儿没人管。来洪合打工的机会,几乎是这家人最后的救命稻草。
这几乎是每个拖家带口来到洪合的家庭,都有的故事。小毛的爸爸6年前就来了,当时,为了不让孩子当“留守儿童”,他把3个孩子都带到了洪合。只是,这个一门心思挣钱养家的父亲压根儿没有想到,孩子在身边待了6年,却和自己越走越远,甚至远到他“完全不知道儿子在想什么”。
也曾经有人想过回乡。
一个贵州女人曾因为孩子学坏,举家搬回老家,可没过多久,她又回来了。“这边行情好时一年一个人挣五六万,差点儿时也有两三万,老家种地能挣多少?能养得起孩子吗?不饿死就谢天谢地了。”
“来洪合是唯一的选择。”刚刚失去龙龙的母亲何丽云说,如果一切可以重来,自己还是会带着龙龙来到嘉兴,因为,“真的没有第二条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