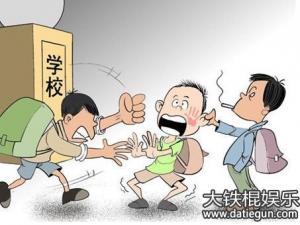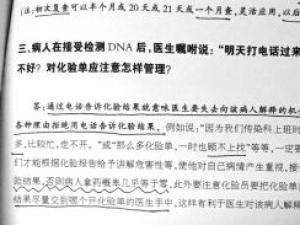《农村寄宿学校“惩戒术” 探秘农村寄宿学校“惩戒术” 学生“自我教育”》是由大铁棍娱乐网(www.datiegun.com)编辑为你整理收集在【社会万象】栏目,于2016-05-16 20:26:23整理发布,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可及时向我们反馈。
原标题:农村寄宿学校“惩戒术”探秘
能否住宿对于农村家庭而言,绝不仅仅意味着农家子女读书方便,还意味着现实收入的增加
为防止被学生贴上体罚的标签,老师一般都不会直接动手,而是让违纪学生之间展开“自我教育”
学校内部底层孩子在抗争中所形成的日常江湖,对官方的处分和警告赋予另外一种“英雄主义”的文化内涵

中国日益开放的中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和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使在外务工人员收入日渐宽裕,且更为重视教育。他们更愿意将子女送到农村家乡所在的中心城镇就学,进而出现了既留守又流动的新格局: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逐步向家乡所在的中间城镇聚集,特大城市中的流动儿童回流,村落校点中的留守儿童上移。村落校点亏空而被撤并、中小城市和乡镇中心校拥挤、大城市学校学位紧缩性持平,将成为中国当下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不可避免的教育现实。
在此教育现实中,笔者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西部底层孩子阶层再生产发生的日常机制及策略干预研究》(项目编号:15CSH012)持续深入中国底层乡校,探寻寄宿制学校内中国子代们的日常微观生活世界:在寄宿制学校已经成为中国农村教育半壁江山的宏观背景下,在寄宿乡校演变成为略带福利色彩的资格竞赛游戏中,寄宿制学校中的中国子代们究竟遭遇了何种复杂的校园“惩戒术”,以至于日常管理从“直接惩戒”走向“间接惩戒”直至“故意无视”;在此基础上政府主导推动的自上而下分解式关爱体系又如何屡屡受挫,以至于需要重新反思和检讨:对这群寄宿制学校中规模庞大的中国子代们,如何实施有效的成人世界的关爱。
能否寄宿乡校演变成略带福利色彩的资格竞赛
在农村社会发生巨大转型的城镇化大背景下,农村教育难免经历复杂变迁。在芥县云乡,给底层孩子带来巨大改变的莫过于乡校的大调整。
云乡位于中国西南农业县——芥县的西南部,地跨山地和丘陵,是芥县内最大的山区乡。1986年,云乡有附设初中班中心小学1所,村小4所,25 个教学班,中小学生1040人,教职工40人。1996年,因为乡镇建置改革,原中心小学无法满足新的云乡就学学龄人口,便修建了中心小学教学楼。 2004年,中心小学彻底改制为九年一贯制学校。2005年,龙岩和田坝村小学撤销。目前,全乡有九年一贯制学校1所,10个教学班,在校学生238人,教职工35人,幼儿园1所,入园幼儿30人,教师2人。
显然这是云乡实施“撤点并校”后的结果:一方面源于乡镇撤并,另一方面源于复杂的社会生态。
原有乡校和教学点的撤并,使大批以留守儿童为主体的西部乡村底层孩子就学距离变远。布局调整后农村学校的服务半径大大提高,由过去的平均5公里扩大到10余公里,最远的达到方圆20公里以上。
从云乡的情况来看,随着村小的撤并,从2005年起,全乡仅有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政府于当年投入修建了一栋三层楼的学生住宿楼,一层作为校长办公室、德育室、教务室、澡堂等而被使用,楼上两层则统一用作女生住宿,原新建住宿楼背后靠近山坡一侧的联排平房则统一用于男生住宿。
在云乡学龄人口达到顶峰的2011年,学校床位显然无法满足学生就学的刚性寄宿需求,学校不得不采取措施:一方面严格控制住宿生名额,另一方面将部分闲置的教学用房改造为临时宿舍。部分学生的住宿只能被迫采取“两生一铺”或“大通铺”的方式解决。
尽管如此,学校仍然无法满足撤点并校后云乡学龄人口峰值期的刚性住宿需要。在学期报名前,争取孩子的住宿名额成为云乡家长们纯粹比拼社会资本的重要公共活动。
根据笔者对云乡学校的调查发现:部分家其实就在距离学校后山100米的学生可以入住学校,而个别家校距离在4公里以上的学生却无法入住。这背后是不同农村家庭之间社会资本的比拼。
能否住宿对于农村家庭而言,绝不仅仅意味着农家子女读书的方便,还意味着现实收入的增加,对贫困的村落底层家庭而言则尤其重要。它甚至能决定一个家庭的全部命运,云乡蜈村的张广刚家庭即是此类的极端案例。
云乡和全国其他诸多农村社会一样,因为日益严峻的农村男性光棍危机,使农村日益增多的适婚大龄男青年难以娶妻。在残酷的婚姻竞争中,当时38岁的张广刚由年迈的父母张罗,迎娶了邻村精神病患者刘霞。4年后,刘霞诞下儿子张浩。彼时,年迈但尚健康的父母还能帮着照顾孙子和儿媳妇,张广刚得以到新疆务工赚钱。
张浩8岁时,必须要入读小学一年级。70多岁的爷爷奶奶无力每天接送他去离家近6公里外的中心校就学——按照国务院相关系列文件规定,农村小学 1至3年级学生原则上不寄宿,就近走读上学;小学高年级学生以走读为主,确有需要的可以寄宿;初中学生根据实际可以走读或寄宿。
在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中,三年级以上的高年级学生住宿尚不能全面保证,更不要说像张浩这样的一年级就读者申请住宿了!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学校生活教师严重不足,仅有的两名住宿管理老师由德育处主任邓畅老师和其在附设幼儿园担任专任幼儿教师的妻子张丽负责,低龄住宿几乎很难保证现实安全,更不要说事无巨细的日常照理;另一方面,国家政策也给予了原则性的反对。
各种现实因素使张广刚被迫从新疆回到四川云乡,承担起每天接送张浩的责任。无法外出务工赚钱的张广刚,只能在家从事收益率极低的农业生产。这样的状况显然至少还要维持到张浩上小学三年级有资格申请入中心校住宿为止。
张广刚家庭属于低年级住宿被政策和现实所拒斥者,但他需要由自身家庭,实质上只能由他来独自承担由地方大规模撤点并校所带来的额外生活负担和经济收入减少的代价。而对于高年级住宿者而言,他们也并非保有理所当然的实际住宿权。
自2006年实施“两免一补”政策、2008年实行城乡义务教育全免费以来,各地农村学校寄宿已彻底免费或给予不低的住宿生生活补助,在农村学校寄宿已不能构成农村家庭的经济负担,相反,这种不用由一个家庭成年劳动力每天接送的现实,确实解放了劳动力,有助于家庭成员全身心投入到各种能够增收致富的日常实践中去。
上学距离变远,使底层孩子能否寄宿乡校日益演变成为一项略带福利和奖励色彩的资格竞赛,同时,惩戒也悄悄与住宿搭建起了内在复杂的关联。
“痛并快乐着,长点记性”的传统惩戒方式
农村学校布局结构调整重心上移至乡镇,使底层乡校规模日益增大,但学校管理却面临现实压力:一方面建有教师周转房的县更可能将房子建于县城—— 既可形成集约效应,又可吸引新教师留任,而没有周转房但撤并后重心移至乡镇的县,愈来愈多的教师在更为便利的县际交通和更为优越的县城居住条件的刺激下,居住的县城化率逐年迅速提高;另一方面,空编率、教师借调等导致西部乡校日常人手不够的问题仍然十分突出,生活教师配备等问题依然严重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