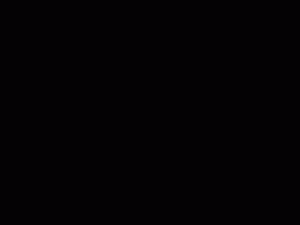《为清除纳粹标语被打 大妈为清除纳粹标语30年跑遍德国 曾被打伤颅骨》是由大铁棍娱乐网(www.datiegun.com)编辑为你整理收集在【社会万象】栏目,于2016-09-18 10:21:41整理发布,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可及时向我们反馈。
为清除种族主义与纳粹标语,她跑遍德国甚至去其他欧洲国家
2016年9月1日。
喂完三只猫,挎上相机,70岁的德国退休女教师伊梅拉。门萨-施拉姆关上家门。提着的白色布包里,装着刮铲、涂鸦喷漆和香蕉水。
她在柏林的街头四处张望。
灯杆、护栏、街墙、邮筒、广告牌……

她寻觅着,那些含有纳粹和种族主义的贴纸和涂鸦:“德国是德国人的”:“外国人滚开”:“关闭难民营”……
发现了,施拉姆就先用相机拍下来,记录下时间和地点,然后,把它们一点点撕下来,或者,用刮刀铲除。
如果是涂鸦,就用喷漆把它们覆盖。
德国的网友把施拉姆称为“喷漆奶奶”(S p ra ye r-O m a)。但她更喜欢自称“政治清洁工”(P olitputzer)。
过去3 0年,施拉姆跑遍了德国,甚至去欧洲其他国家,跟“新纳粹”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巷战”。
她被“敌人”打伤过,也遭遇到不解与反对。有些地方的当权者也不欢迎她的出现。
她从未“缴械投降”。
她越挫越勇。
战争
30年前,9月1日,施拉姆去上班。
在家门口的公交车站上,她发现了一张贴纸,上面写着要求“释放纳粹副元首鲁道夫。赫斯”的字句。
赫斯曾与希特勒在同一监狱服刑。在狱中,他执笔撰写了希特勒口述的《我的奋斗》一书,并成为希特勒的心腹。
施拉姆生于斯图加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图加特的市中心几乎被空袭完全摧毁。
施拉姆一岁时,欧洲国际军事法庭在德国纽伦堡宣判,赫斯终身监禁。
看到这张贴纸,施拉姆感到震惊。但她没有撕掉那张纸。在公交车上,她为此自责,“那有一张宣扬纳粹的贴纸,你为什么不把它撕掉?”
一整天,她都忘不了这件事。
下班回家,那张贴纸还在。施拉姆用钥匙把它刮掉了。“当时有一种奇妙的感觉,我至今都还能体会”。
施拉姆的“战争”打响了。
下班后,或者周末,她开始在西柏林到处搜寻那些含有纳粹和种族主义的贴纸和涂鸦:“德国是德国人的”:“外国人滚开”:“关闭难民营”……,将其清除。
那种被痛恨和被视为异己的“不舒服”曾发生在她的身边。
施拉姆的父母离异,她在寄宿学校长大。她姐姐嫁给了一位印度裔德国人。结婚前,学校的老师居然劝她,一定要阻止。因为“德国家庭中不应掺入外国人的血”。还有邻居对她的姐夫说,“洗洗吧,你像一只肮脏的猪”。后来,她在柏林一所特殊学校任教,学生都是精神受损的孩子。
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她认为,这是自己的使命,并尽其所能。
施拉姆说,她坚持这样做的目的,不仅仅是让仇恨消失在街头,也想引发人们反思,最终让仇恨消失在人们心中。
开始,没人觉得,施拉姆能打赢这场战争。
在街上,清除贴纸,常常有人骂她。
有一次,她在路边清除纳粹标志,有个年轻人向她走来。“你在做什么?”
“我正在清除一个纳粹字符号。”
“不,它应该留在那儿。”
“不,应该清除。”
“我跟您说过了,它应该留在那!”
“已经晚了!因为现在它已经被清除了!”
年轻人环顾四周,冲向她。施拉姆慢慢走向对方,在他面前站定。“我开始无所畏惧地笑,并直视他的眼睛。他就像受到惊吓一下,转身就逃走了。”
讲述这个故事,施拉姆的脸上充满骄傲。
1992年,在火车站,当她用喷漆清除一处仇恨标语时,柏林交通公司的安保人员甚至推搡她,弄伤了她的颅骨。
威胁与恐吓,发生在街头的隔空对话。
德国媒体报道说,新纳粹组织痛恨她。至少在柏林地区,右翼组织里的人都知道她。他们掌握有关她的一切:长什么样,住在哪里。
在柏林西南,差不多100个地点,曾出现印有施拉姆照片的贴纸,上面写着:“施拉姆刮吧,你拿我们根本没办法”。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施拉姆得了癌症。
疾病没能阻止她。她的主治医生甚至建议她,继续做下去。他认为,这种心理激励,有一定治疗效果。
2006年,退休后,施拉姆全身心投入这场“战争”。
2013年,德雷斯顿的反新纳粹游行。
一名新纳粹分子,举起一块大石头,狠狠砸向施拉姆的脸。只差一厘米,就砸中她的眼睛。
“当时,我完全震惊了。”
施拉姆说。
“我不会表露出我的恐惧。”
仇恨
施拉姆没有儿女。
离婚的她独居,三只猫陪伴着她。
柏林西南市郊的不少人,都曾见过她———这个提着白色布袋到处游荡的老太太。
有人和施拉姆打招呼:
“您又来乱涂乱画了?”
“什么?乱涂乱画?!”
“这里写着‘外国人滚开’,我要涂掉这些东西,我可以这么做!”
“您别管,这样挺好的,我的生活没有受影响。”
“我不愿意,我不可以,我也不允许这样生活”。
很多人直言不讳地告诉施拉姆,那些涂鸦者,或贴那些贴纸的人,都应该享有言论自由。
施拉姆针锋相对,“言论自由是有限度的,当仇恨产生的时候,言论自由也就不复存在了”。
上学时,柏林的凯文曾帮助施拉姆清除纳粹标语。
但多年之后,两人再次相见,是在一次右翼组织的游行中。凯文正在学校周边,散发德国右翼政党德国国家民主党(N P D )的宣传品。他已经归顺“敌营”。
他还组建了一个名叫“仇恨核心战士”的小团伙。那年,才17岁的凯文,已成为“N P D”在柏林斯潘道区分支机构的财务主管。
尽管德国刑法典86条规定,在德国境内展示纳粹标志的人将面临最高三年的徒刑或罚款。但总有人使用各种各样的替代暗语,逃避这一条款的制约。
同样在街头活动,凯文说,他从未被德国警察找过麻烦。
但好几次,德国警察对施拉姆说,“你没有权利把这些东西撕掉”。施拉姆以牙还牙,“没有人有权利贴这些东西,而法律也没有禁止我撕掉”。
有一次,施拉姆正在喷漆覆盖在一堵废墙上的纳粹标记和种族主义标语时,有位优雅的老先生走过来对她说,“您比纳粹更差劲!”后来,他还报了警。
警察让施拉姆立即停止,否则将面临指控。
施拉姆告诉警察,“告我我也可以活得很好”。
她回家,等了几周,没有什么指控。
于是她出门,继续清除那片标记。
但处罚和官司,一直伴随着她持续多年的“战争”。
1995年,有个18岁的姑娘,在快轨上,看到施拉姆提着一个写着“反对纳粹”的布袋。
她开始咒骂她,对她行纳粹礼。
施拉姆举起相机拍照。
女孩下车,向站务员报警。站务员停下了列车,让施拉姆也下车。警察到场,了解情况后,女孩遭到指控。
“但法官却在法庭上对我说,您拿着这样一个袋子在外面,也不奇怪有人会给您行纳粹礼”。而最后,法官称理解女孩的举动,拒绝对其进行处罚。
施拉姆觉得荒谬极了。
“纳粹分子有言论自由,而我却没有。”
去年,在一次新纳粹的游行示威活动中,施拉姆对30名新纳粹支持者竖起了中指。
对方以人格侮辱将她告上地方法庭。
最终,对方在最后一刻撤销了这次诉讼。
现在,施拉姆还面临着一起官司。号称不支持种族主义、不支持仇外并反对极端主义的德国组织———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P E G ID A )控告她损坏物品。因为施拉姆在他们的涂鸦上动了两个字母:把“M erkel m ussw eg”(默克尔必须下台)改成“Me rk e!H a ssWeg”(注意!仇恨消失!)。
说起这个,施拉姆忍不住笑了。
她说,“所有在我清除涂鸦和贴纸过程中弄坏的东西都是可以修复的,然而人的尊严是无法修复的”。
玫瑰
她已经是满头白发的古稀老太。
现在,她仍然在街角,笨拙踮起脚尖,蹦跶着伸长手臂,奋力够向高处,吃力地摇摆上身,铲除新纳粹标签和一切排外的标语。
每个月,施拉姆从退休金中拿出30 0欧元,购买清洁工具和涂鸦喷漆,外出行动的车票和打印照片的费用也从中支付。她外出行动,前夫会来照看她的猫。
在柏林,每周,她会花上25个小时干这件事。
如果到其他城市,每周,她会花上40个小时。
在萨克森州,有一天,她曾干了整整16个小时。除了睡觉,就是清除贴纸。
有人觉得她“疯了”,更多人觉得什么都改变不了。
施拉姆的回答则是:一是要告诉纳粹分子,停下,这里有人不同意您的看法;二是要告诉被仇视的人,你们拥有我们的支持和团结;三是要告诉冷漠的旁观者,如果什么都不做,是什么也改变不了的。
10多年前,她开始记录并统计自己清除的“仇恨贴纸”。至今,数量已达7.4万多张,装满了80多个文件夹。
她将收藏的数万枚“仇恨贴纸”展出。
这个名为《毁灭仇恨》的展览已在德国各地巡回展出了100多场,今年7月,作为“德国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1880年以来”展览的一部分,在德国历史博物馆展出。
过去30年,施拉姆的美好回忆也不少。
有一天,施拉姆清除了200张贴纸。街头,一位年轻人朝她走来。她认识他,新纳粹分子,曾多次威胁她,甚至想要攻击她。他可能就曾是那些在她家墙外涂画“施拉姆,我们抓住你了!”的年轻人之一。
他突然对施拉姆说:
“施拉姆女士,我再也不是他们的一员了。我再也不想和他们有任何瓜葛,我还想谢谢您”。
施拉姆哭了。
“你为什么想通了?”
“我总是给您带来压力,但是您还是毫不动摇,一如既往,让我开始思考。”
还有一次。
一场研讨会后,有年轻人朝她喊:
“施拉姆女士,您是世界上最好的女人!”
还有一次。
有位优雅的绅士,在看到她在街头撕贴纸,当着太太的面,拥抱了她。
柏林郊外的一些社区,人们受到她的感染。
他们拿起了施拉姆最喜欢的武器“刮刀”,每个月定期散步,清除纳粹贴纸。
施拉姆并没有办法彻底摧毁仇恨。
但她认为,她至少达成了一个目标:很多德国人都意识到,仇恨是被煽动起来的。
她的举动至少让德国人变得比较敏感。
她和不少中小学建立联系,成为校外导师,办讲座,给学生开办工作坊,教孩子们将纳粹涂鸦改成有爱的艺术画。“这让孩子们会对身边这些仇恨变得敏感”。施拉姆向孩子强调,请不要“用仇恨去反仇恨”。
施拉姆获得过几项荣誉,如德意志联邦雄鹰奖章。不过,她后来又还了回去,因为一名国家民主党前政客后来也获得政府这一表彰。
她说,“那些控告才是我最好的嘉奖”。